他统治期间采取了什么策略-宋太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 (他的统治被称为)
作为开国君主,宋太祖在统一大局巳定的情况下也没有志满意得、忘乎所以,平定南方诸国后,各国的金帛财宝源源不断地运至东京,宋太祖将它们作为战备物资,全部收贮在内库,从不随意挥霍,宋太祖本人有射猎和職衡,踢...
作为开国君主,宋太祖在统一大局差不多定下来的时候,也没觉得自己特了不起,忘乎所以。平了南方那些国家后,各地的金帛财宝就哗哗地往东京运,宋太祖把这些都当作战备物资,全收在内库里,自己从不乱花。他这人吧,喜欢射猎和踢球(那时候叫蹴鞠),刚当皇帝那会儿,手痒得不行,老叫上几个手下一起玩。下面咱就聊聊他这几件事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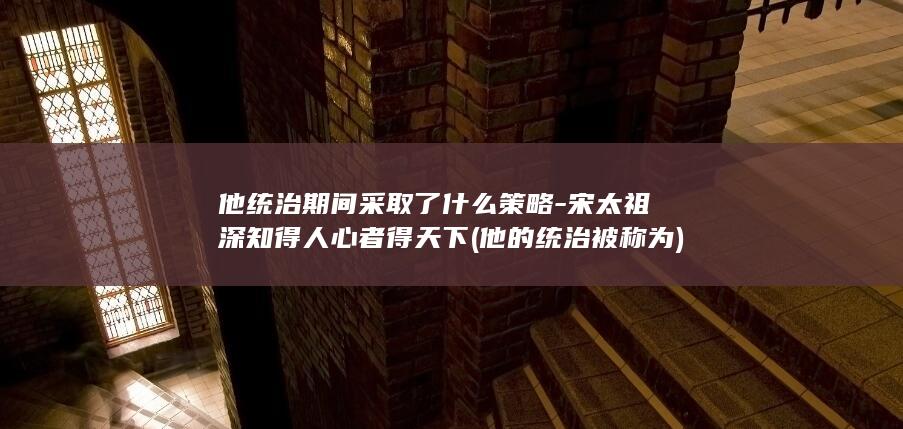
有一天,宋太祖在后苑射鸟呢,有个大臣跑过来说有急事求见。太祖接过奏章一看,哎,也不是什么马上就得办的事儿,当时就有点不高兴,训了那大臣几句。结果那大臣还挺犟,回了一句:“奏章里的事吧,也不是非得马上办,但总比射鸟要紧点儿吧?”太祖一听更火了,顺手抄起一把玉斧就扔了过去,正好砸在那人嘴上,门牙掉了两颗。这人也没吭声,就跪地上,把捡起来的牙齿揣怀里了。
太祖问他:“你想拿这个去告我啊?”那人说:“哪敢啊!不过您现在是天子,一言一行都有史官记着呢。”太祖一听,愣了一下,对啊,当皇帝的,说啥做啥都重要,赶紧把人扶起来,道了歉。打那以后,他慢慢就把射猎和踢球的爱好给戒了。
宋太祖这人挺明白,得人心才能得天下。他在位的时候,搞了个“布声教”的策略。说白了,“布”就是多施点恩德,“声”就是该立威时就立威,恩威一起用。
他特别会拉拢人心。陈桥兵变后,太祖刚进皇宫,看见个宫女抱着个小孩,是周世宗的儿子。他问旁边的赵普、潘美这些人,这孩子咋办。赵普说斩草除根,潘美在旁边不说话。太祖问他,潘美还是不敢吭声。太祖说:“咱把人家的皇位夺了,再把他儿子杀了,我这心里实在有点过不去啊。”潘美这才说:“我也在世宗手下当过官,让我劝您杀这孩子,我对不起世宗;不劝您杀,您又可能觉得我不忠心。”太祖摆摆手:“你把这孩子带回家,当自己侄子养吧。”
有次宋太祖办国宴,前朝翰林学士王著喝多了,在席上大吵大闹,有人劝他收敛点,他突然跑到皇帝屏风前大哭起来。太祖也没生气,让人把他扶出去了。有大臣说,前朝遗臣在宫里哭,肯定是思念周世宗,得治罪。太祖不以为然,说:“王著就是个书生,我了解他的为人,这事儿别提了。”后来王著酒醒了,知道没被杀,从此就死心塌地跟着太祖了。
作为武将出身,赵匡胤知道让士兵抢掠肯定惹老百姓反抗,所以打仗时总告诫士兵别乱杀人。平后蜀的时候,有个叫王全斌的宋将在城里杀了不少人,还让士兵抢东西,结果后蜀老百姓反了,太祖就治了他的罪。
曹彬围金陵的时候,太祖三番五次传旨:“别伤城里的人!”金陵老百姓的命和财产都保住了。平江南的消息传到朝廷,大臣们都来祝贺,太祖却哭了,说:“老百姓以前受割据的苦,我用‘布声教’安抚他们。可攻城的时候,肯定还有人死在刀兵里,我心里难受啊。”
赵匡胤跟少数民族打交道,也用“布声教”。党项族在西北边儿,他们的节度使李彝兴想跟宋朝搞好关系,就送了300匹好马。太祖挺重视,赶紧让玉工打条玉带回赠。他还特意问党项使者:“李彝兴腰围多少?”使者说:“我们元帅腰可粗了。”太祖笑了笑:“哈哈,看来你们元帅是个有福气的人啊。”让人打了条“跟抱着的树那么粗”的玉带。
使者把玉带回党项,李彝兴特别感动,说以后一定效忠宋朝。后来宋军打北汉,他果然帮了大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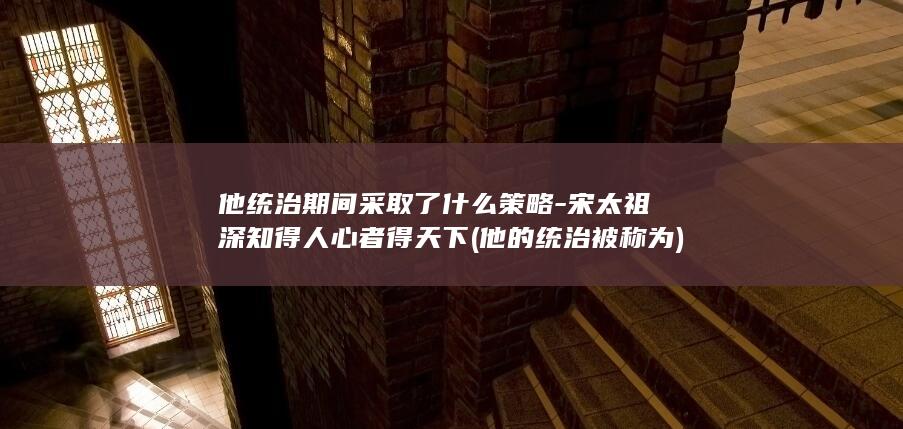
为了边境安宁,赵匡胤对周边少数民族“好好安抚”,那些不听话的大臣,不管功劳多大,都换掉。灵武节度使冯继老爱抢羌人的羊马,惹出乱子,太祖就把他撤了,换段思恭去。段思恭改了冯继业的毛病,按太祖的意思好好安抚羌人,边境安定了。段思恭也因此得了不少赏。
为了加强中央集权,不让节度使再像唐朝那样胡来,让宋朝能长久,太祖搞了一堆政治军事改革。“杯酒释兵权”只是个开头,后来又搞了三样主要的改革:
第一,建枢密院。枢密使和副使管调动全国军队,分掌军权。三衙管禁军,但不能调兵发兵;枢密院能调兵,但不能直接管军队。这样调兵权和领兵权分开了,互相牵制,皇帝好控制军队。
第二,内外相维。把军队分成两半,一半驻京城,一半守各地,但京城军队比任何一个地方都多,随时能平外地叛乱。外地军队合起来又能抗衡京城军队,这样内外互相牵制,谁也别想造反。
第三,兵将分离。用“更戍法”,京城和外地禁军都得定期调动。京城士兵轮流去外地或边境,士兵老换防,就不认得将官,将官也没法在士兵里立威,当然就不能带兵对抗朝廷了。
为了削藩镇,太祖用了“强干弱枝”的办法,主要有:
第一,削夺权力。把节度使兼管的州郡划成京直辖,派文官当知州、知县,直接对中央负责,不听节度使的。那些一直占一方的节度使,太祖也用“杯酒释兵权”的办法一个个罢免了。
第二,管住钱粮。把地方财权收中央。宋朝在各路设转运使,一路的钱除日常开销,全上交中央。
第三,收走精兵。各州把藩镇里能打的士兵送到京城补禁军,又在地方招壮丁到京城当禁军,这样中央禁军全是精兵,地方就剩下老弱病残,编成地方军,没法跟中央抗衡了。
官僚制度方面,削弱宰相权力。太祖刚当皇帝时,宰相奏事还能坐着。有天早朝,他对宰相王溥、范质说:“我眼睛有点花,你们把奏疏拿上来。”等范、王二人站起来,侍卫悄悄把他们的座位搬走了。之后宰相在皇帝面前也得站着奏事。太祖不光从形式上降宰相地位,还把宰相的军权给枢密院,财权给三司使,宰相就管民政了。
削弱相权的同时,百官里搞“官、职分离,互相牵制”。比如设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、三司副使,当宰相、枢密使、三司使的副手,各部门长官互相牵制。宋朝官制里,“官”是品级,领俸禄;“职”是殿阁、馆阁学士之类的荣誉,没实权。只有皇帝或中书省“差遣”的临时职务才有实权。任官时职、权分离,名、实混着,谁也没法把权力、荣誉、威望集一身,权力大的不一定职高,职高的可能没权力。
为了扩大统治基础,太祖改革了科举考试。宋朝初年,科举范围放宽,不管家里穷富,有文化都能去考。他还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,防权贵子弟作弊。
太祖还改了重武轻文的风气,刚即位就下令修孔庙,开儒馆,用名儒。针对五代时文教废、学校荒,他拨款修国子监学舍,开学那天还派人送酒祝贺。他认为,乱世用武,治世用文。后来文教兴盛,科举人多,大批文人进统治集团,文臣慢慢取代武将,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了。
太祖搞的这些改革,让宋朝中央集权加强了。统一安定的局面,给后来经济、文化发展打了好底子,他创的这套办法,成了宋朝后代奉行的“祖宗家法”。
不过,太祖这些防弊、立国的法,也有不好的地方。“杯酒释兵权”让武职官员成了摆设,兵不识将,将不识兵,虽然防了军队政变,但削弱了部队战斗力。官僚机构重叠,互相牵制,造成“冗官”“冗费”越来越多,办事效率还特低。到了北宋中后期,太祖的“祖宗家法”终于让国家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局面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