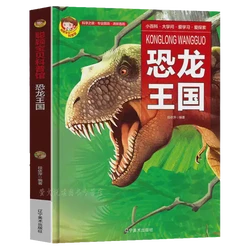凌晨两点,录音室的红灯像一只充血的眼睛,死死盯着天花板。窗外的雨下得很大,噼里啪啦地砸在铝合金窗框上,声音有些发闷。我坐在控制台后面,手里捏着一罐早就凉透的咖啡,盯着面前那台老式的开盘录音机。磁带转动的沙沙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,像是有无数只细小的虫子在啃噬着耳膜。说起来,这活儿我也干了半年多了。

凌晨两点的这个城市,总会给人一种迷离的感觉。不管是加班到深夜的白领,还是失恋的姑娘,都喜欢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,让我讲讲故事,陪她们聊到睡着。但今天,给我打电话的是老张。老张是个挺有意思的人。
在当下短视频和脱口秀盛行的时代,他却依然坚守着传统的评书艺术。他不讲那些传统的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,而是专注于讲述一个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。更让人称奇的是,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,非要等到午夜十二点到凌晨四点之间才开始录制。他说这个时候阳气最弱,阴气最重,故事的灵魂才能更好地附着在磁带上。
"滋啦——" 磁带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,把我从思绪中拽回来。我伸手调低了音量,转头看向麦克风后方。老张穿着洗得发白的深蓝色中山装,手里摇着一把折扇。他没戴眼镜,眼神浑浊,嘴唇一张一合,声音沙哑却带着奇异的穿透力。"各位看官,上回咱们说到这荒郊野岭的破庙里,有个叫阿贵的小伙子,正躲雨呢。"
老张的声音低沉而有节奏,仿佛在讲述着评书特有的故事,他描述的雨势之大,雷声轰鸣,闪电划破夜空,将那破庙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明亮。我听着,心中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,觉得这故事情节虽然经典,但多少有些老套,无非是荒庙、孤男寡女、雷雨夜这些老掉牙的桥段,像是把恐怖片的经典元素直接搬进了评书里。就在这时,门外传来了‘咯吱、咯吱’的响声,打破了夜的宁静,阿贵似乎在思考着雨何时能停。
老张停顿了一下,故意拖长了尾音,手里的折扇轻轻敲击着膝盖,低声说道:“这声音,听着像是什么东西在地上爬。”我盯着监控屏幕,屏幕里老张的脸上没什么表情,但他的背脊微微弓着,就像一只随时准备捕食的猫。老张突然提高了嗓门,吓得我差点把咖啡洒出来,“阿贵胆子真大,探出脑袋往外一看,好家伙!只见那庙门口的泥地上,竟然爬着一个人!不对,虽然看起来像个人,但那手脚怎么是反着长的呢?”
阿贵一听到那东西说话,吓得魂飞魄散。刚想往里缩,就听见那东西说话了。声音尖细尖细的,像是用指甲刮玻璃:"借个火......"老张正在说着呢,突然停住了。录音室只剩下雨声和磁带转动的声音。
感觉空气都凝固了。随便看一下墙上的挂钟,两点十五分。老张?我试探性地喊了一声。
老张没有反应。他还是保持着那个姿势,手里的折扇停在半空,头微微偏向左侧,仿佛在听什么人说话。"老张,你没事吧?是不是累了?"我有些担心,站起身想过去看看。
就在我准备按下对讲键的时候,老张突然开口了。但他说的不是故事里的台词,而是一句让我毛骨悚然的话。“这雨,好像停了。” 我愣了一下,走到门口,伸手去推那扇隔音门。门把手冰凉刺骨,像是握住了一块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猪肉。
我轻轻一推,门开了。走廊里空无一人,只有应急灯发出淡淡的绿光。雨水顺着走廊的窗户流进来,在地板上汇聚成一小滩水渍。"老张?"我叫道。
没有人回答。我转过身,回到录音室。老张不见了。我快步走到控制台前,拿起对讲机:“老张?你在哪?
突然间,只剩下对讲机里的电流声。老张啊,你出来一下啊。我慌得不行。
这位老先生虽然有些古怪,但从不迟到,也从不无故消失。我环顾四周,发现录音室里只有我一个人,那把椅子依然稳稳地放在那里,似乎刚才坐过的人根本就不存在。突然,我注意到麦克风下面的桌子上多了个东西。
那是一把折扇,扇面上画着一个穿着红嫁衣的女人,她背对着我,仿佛在凝视着窗外。她的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红线。我猛地回头,看向麦克风,老张的声音突然在耳机里响起,不再是那熟悉的沙哑男声,而是一个尖细的女声,带着哭腔,急切地请求:“借个火……”我猛然一惊。
” 我尖叫一声,把折扇扔了出去。那折扇落地,在地板上滚了几圈,竟然自己立了起来,像是一个站起来的鬼魂。就在这时,我听到录音室角落的阴影里,传来了一阵细微的笑声。
“嘿嘿嘿……”那笑声仿佛带着湿意,轻轻地环绕在耳边,仿佛喉咙里含着水。我惊恐地四下张望,却什么也看不见。窗外的雨声突然变得喧闹起来,像是无数人拍打着窗户。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惹上了麻烦,我急忙抓起桌上的对讲机,准备出去报警。
我的腿像灌了铅,动弹不得。老张的声音突然从四面八方传来,这次是直接在耳边响起:"故事还没讲完呢。"我猛地回头,发现录音室的门不知何时已经关上。门缝里渗出暗红色的液体,像是血,又像某种工业颜料。
老张的声音突然变得阴森,质问道:“阿贵没走,你为什么要走?”他接着解释道,阿贵是因为这里太冷,想找个伴儿。我被吓得后退,直到背部撞到了控制台上。绝望中,我抬头看向那盘正在转动的磁带,上面的磁粉正一点点脱落,变成了黑色的粉末,在空中飘散。我颤抖着辩解:“不……我不是阿贵……”
“你不是阿贵?”老张冷笑了一声,“那你是什么?你是那个想听故事的人,对不对?” 突然,录音机里的磁带发出了一声巨大的爆响,像是有人在里面撕扯着什么东西。“咔嚓!
录音机突然停了,整个房间陷入了一片绝对的黑暗。只有那把立在地板上的折扇,在黑暗中隐隐发光,散发着一种诡异的光芒。我听到了轻柔的脚步声,缓慢而沉稳,从录音室的最深处逐渐向我靠近。
“咚、咚、咚。”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口上。我闭上眼睛,拼命地祈祷,祈祷这是一场噩梦,祈祷这只是一次恶作剧。可是,那脚步声越来越近,越来越清晰。
我感觉到一阵寒意扑面而来,那股寒气里夹杂着泥土的腥味和腐朽的气息,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我听到头顶上方传来老张的声音,那声音在黑暗中幽幽响起。我猛地睁开眼睛,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录音室。站在一条幽暗的小巷里,脚下是湿漉漉的青石板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评为腐朽气息。
天空阴沉沉的,乌云密布,雨点像鞭子一样抽打下来。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头,他手里的那把折扇上画着红嫁衣,正笑眯眯地看着我。"老张?"我难以置信地喊道。
老张转过身来,脸上没有五官,只有一张大嘴,裂开到耳根。他咧嘴一笑,露出一口黑牙,开口说道:"各位朋友,今晚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"说着,他举起折扇,指向我,接着说道:"下回分解,咱们就说说这个新听众,是怎么变成故事的。"话音刚落,他猛地一挥手,那把折扇化作一道红光,直奔我而来。
我下意识地举起双手挡在脸前,惊呼一声:“啊——!” 随即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,大口喘着粗气,全身被冷汗浸透。我环顾四周,仍惊魂未定。窗外,那场暴雨仍在激烈地落下,雨点不断敲打着窗玻璃,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
我从梦中惊醒,急促地喘着气:"呼……呼……"。等我回过神来,这才意识到,自己的心脏还在剧烈地跳动。这竟然只是一场梦?我这才松了一口气,伸手去拿桌上的水杯。就在这一瞬间,我的手停住了——我看着自己的手,上面沾着一些黑色粉末。
我突然抬起头,目光落在客厅的角落。那里摆放着一台老旧的开盘录音机,这是老张送给我的礼物,据说是他用了几十年的宝贝,能够录下最真实的声音。此时,录音机里的磁带正缓缓转动着。
我屏住呼吸,凑近了听。“列位看官,上回咱们说到这荒郊野岭的破庙里……” 那个沙哑的、熟悉的声音,正从录音机里传出来,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回荡。而在录音机的旁边,静静地放着那把画着红嫁衣的折扇,正对着录音机的麦克风,轻轻摇动。窗外的雨,越下越大了。